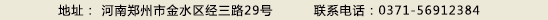怎样利用优化叙事动力,来提高电视剧创
作为一个从实践中来的理论命题,关于“电视剧叙事动力”的探讨,也具备从理论回归实践、指导实践的可能。
因此,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是“怎么办”的方法论问题,即“怎么通过电视剧叙事动力生成电视剧叙事”。进一步说,就是怎么通过电视剧叙事动力层面的优化,生成更加优质的电视剧叙事作品。
如果说,从文本现象中演绎理论,是“行易知难”;那么,基于理论认知提出实践策略,就又有了“知易行难”之嫌。
通过前文中的、种种讨论,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优化“叙事动力”是电视剧创作中关键的提质之道。
但同时,当我们明白“叙事动力”的重要性,想要针对性地提升它时,或也可能是困难重重。
在业界,对于广大电视剧创作者来说,他们也许不太清楚此“叙事动力”,但一定十分了解彼“叙事动力”,他们有常规的、也有带有个人色彩的“叙事动力”创造理念及方法。
也就是说,与“叙事动力”相仿的概念在实践中早已存在,就体现在从始至今、不计其数的鲜活文本中。或许,在电视剧编剧、导演等人士眼中,笔者当下所谈,仅是“纸上谈兵”。
他们也许会想,“既然我们有,为何要信你那一套、听你的”。
对此,笔者表示一定的认同,因为研究者和评论家即使观察再多、讨论再多,终究不是“作者”,不能亲自创造,一些理论见解并不见得都能在实践中落实。
但也想申明的是,理论并不是实践的被动反映,理论的有效性不是由实践的有用性决定的。
比如,创作者多是明事理的,但制片方却不尽然。制片方追求的是利润,他们对“理论”的诉求,是一套免费的、开源的“专利”,以供赚取利润。当“理论”不能创造利润,不能做工具用时,即便有益,也会被认作无效。
因此,笔者在此并无意提供某种不切实际,又带有指手画脚嫌疑的“策略”,而只是希望能相对清楚地阐明原理、点出症结,仅提供“解题方向”,而不是“替人作答”。叙事动力,有总分、强弱、显隐之分,自也有优劣之别。
所谓优劣,事关叙事动力生成之叙事意义的审美价值。每一部电视剧都存在叙事动力,却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优质的。想要优化“叙事动力”,势必要先论其中不足。在此,不妨先结合一些“低质量电视剧”叙事动力上的问题,做以简析。
比如,电视剧《雷霆战将》(豆瓣评分2.2分)号称是“青春版战争史诗力作”,却在开播不久旋即被下架,原因是剧情与革命历史严重偏离。
剧中人物“抹发胶、住别墅”,剧情也被批将“偶像剧”套路用在抗日题材上,人物失真、情节失实,就算设置再多的矛盾冲突,有效的叙事动力也极为寥寥;
翻拍自同名日剧的电视剧《深夜食堂》(豆瓣评分2.9分),被批“中国演员、日式故事”、情节尴尬、价值观陈旧、硬性广告植入等,显然没有延续同名作品的声誉。
情节“生硬”的“复制”,令多数观众感受到侮辱,故而愤愤不平地打出低分,说明该剧可谓毫无吸引力,更勿论叙事动力。
同样的负面案例,在豆瓣低分电视剧中还有很多,如演技浮夸、剧情离奇、镜头质感平平的《甜蜜暴击》(豆瓣评分2.9分),败坏“经典”的《新寻秦记》(豆瓣评分2.9分),价值观惹得大众生厌的《生活像阳光一样灿烂》(豆瓣评分2.9分)。
演的像“猴”、情节浅显的年版《鹿鼎记》(豆瓣评分3.2分),情节狗血、内容悬浮的《谈判官》(豆瓣评分3.5分),等等。
这些文本现象侧面说明了,尽管有些电视剧,同样是在叙事、同样有从头至尾的叙事进程、同样是发挥着生成叙事意义的作用,却不意味着它们的叙事动力是充沛的、和谐的,反而更像是多余、无效的。
关于“低质量电视剧”在叙事动力上显现出的具体问题,笔者认为大致有三类:首先,是叙事动力层面的“错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一种修辞性的失当,与故事内容的粗制滥造和失实构造相关,如国产剧领域中的曾持续多年的“雷剧”现象即是此问题的典型反映。
“雷剧”通过造型、台词、动作等方面的夸张失实效果,试图以逆向审丑方式点燃收视爆点,可实际带来的却是低质粗浅的视听效果和流俗媚俗的感官体验,其纵然空有修辞之实,却无修辞之真义,故而因之错用,导致叙事动力无从生发。
其次,是叙事动力层面的“错置”问题,它主要表现为一种进程前进中动力设置的失衡(如作者/读者动力的不相协调,势能/动能的分布不均等),以及整体叙事情境构建中动力安排的失和(如人物、情节或时空动力间的不和谐因素)。
以国产剧领域中的某些“悬浮剧”为例,此类悬浮化的现象及问题,主要见于一些现实题材剧集中,它们本应如实表现社会现实状况和群众日常生活,但却因“飘在空中、不接地气”,与观众的客观经验严重不符,为人所诟病。
结合叙事动力来看,产生悬浮化的一个主因,便是作者未能有效地把握观众的认知期待,未能真正重视“读者动力”这一极。
此外,势能和动能之平衡调用,也在于叙事交流,需要以观众认为的恰到好处为准衡。
另外,悬浮化的另一原因,在于人物、事件与场景时空内在逻辑及秩序的背离,即便前者可圈可点、动力充足,也会因与后者的失和,导致整体的动力效果产生内耗。
再次,是叙事动力层面的“错立”问题,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价值失却。当叙事动力在本身构成上无错时,如果它的运用在方向上存在问题,依然会影响整体的作用效果。
以“同质失趣”现象为例,内容同质的直接结果是美感同质,导致故事丧失审美趣味和文化魅力。当一部剧第一次成功运用某一情节模式或戏剧手法时是创新、经典的,但当此模式出现后仍千百遍、不厌其烦地使用,就是套路化、流俗化的。
叙事层面拼贴复制和表意元素重复出现,会消耗故事内在的原创价值,降低作品内在趣味性,影响审美活动发生。归根结底,叙事动力,是一种艺术力量。
机械刻板的叙事运动中,固然也有动力,但若毫无艺术价值,不仅难堪其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电视剧叙事动力,体现于叙事进程中的创作者/接受者施动、文本受动。在修辞意义上,就是创作者通过作品向观众叙事。
叙事动力是否优质,很大程度在于作者能否恪守本分的通过声画、表演修辞向观众示以诚意,而不是让观众失望。毫无疑问,作者是最懂创作的。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烂剧”的创作者真的不懂创作、不顾观众感受么?不见得。
在国产剧的生产领域中,生产者们其实是最以受众为中心的,他们历来都是以“受众思维”行事的,只不过对于“受众”的理解也许会于真实的受众存在较大的偏差,这也是为何那些本来拍出来是为了迎合观众的电视剧,最后却落得骂声一片的原因所在。
多数情况下,国产剧的创新都是在打着适应受众需求的口号进行的,这种虚构的“受众观”所假设的是受众永远是“喜新厌旧”的,认为用形式上的“花里胡哨”就可以替代内容上的“精神满足”,这一点是大错特错的。
因为,国产剧的观众在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他们会为新颖的形式的所吸引,但持续追剧的动力获取还是需要由内容及其艺术性内核来提供,审美的作用和力量是永恒永在的。
因此,不必假创新与迎合之名行虚悖之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道理,至今依然没有过时。
笔者认为,之于电视剧创作,优化“叙事动力”的提质之道的根本,在于从“作者与观众叙事交流”角度重视“叙事修辞性”问题,即要对每一维度,甚至每一处叙事修辞负责。
比如,在表演修辞上,当演员的表演存在问题时,只会让观众出戏而不是入戏,即便是再优秀的剧本,都不足以支撑起故事,“一个人毁一部剧”;
在视听修辞上,一些言情剧、偶像剧中,环绕、升格、降格等流俗的镜头展示,以及密布的配乐、人物BGM背景音等音乐效果,可谓是比比皆是。
此类视听风格的过度渲染非但不利于受众的审美感知,太过常见后反而会激起受众的恶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声音运动、影像运动、表演运动是电视剧叙事运动的基本组成,是叙事意义生成的渠道,也是叙事动力注入的路径,唯有“共时维度”是通畅的、没有硬伤时,才能确保叙事动力的生成效率不受折损。
除此之外,笔者以为,优化“叙事动力”的侧重点还包括:
强化(数字)电视媒介框架与电视剧叙事进程的技术性互动,深化对电视剧本体连续性的美学实践,使产生叙事动力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更具助力;
进一步规范电视剧生产的篇幅问题,篇幅长短应因事而定,而不是人工“注水”,中篇、短篇电视剧需要更具形式质感的叙事动力,长篇电视剧则不能只追求量,而忽视质;
在范围上要注重“总体/分支”动力的数量安排和功效发挥,在程度上要注重“强向/弱向”动力的均衡互补,在状态上要看到“显性动力”,也要适当设置“隐性动力”;
在充分认知“作者、文本、观众”关系的基础上,学会更加有效地在叙事进程中做“功”,借助人物、情节、时空,一方面释放势能,另一方面持续注入动能;
在叙事开端,要起动、起因、起喻,起手布局、学会造势,以“副文本”为定势、以“第一幕”为先势、以“第一集”为后势,为后续叙事进程开辟纵深;
在叙事中端,要基于意图和判断的“博弈”延展文本演述,讲求中盘增动,为情节发展创造长效的人物动力、显性的连叙动力,以及复合的时空动力,并
转载请注明:http://www.yuncaibanjia.com/fjcf/139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