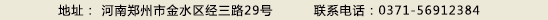平遥本土文学汾河在这里转了一道湾四
怀揣着新郎的绵绵情意和对婚姻生活的无限向往,天快亮了夏丽才勉强合一会儿眼。
晨起,近道儿的七姑八舅们都先客人们之前到了。远处的亲戚有的早两天住下来帮忙,还有抽不开身子的,今儿也都走在路上了。每个亲朋的出行都向着一个目标:汾水湾和芦花荡的典礼仪式,每个人的眉心都张扬着两个字:幸福。
夏丽起床叠好被子,收拾了一番。她拿起苕帚,芳芳过来夺下笑道:“这女子,今日用不着你动手,快脱了鞋体体面面坐着。”农家的女孩儿,勤劳惯了的,一下子皇后似的被供在床上等人伺候,实实觉得不自在。
芳芳把夏丽的鞋放在鞋架子上,对夏丽说:一会儿打送灯的女子们来了陪你,姐姐到外面招呼了昂。”
“喂、喂,新娘子,我们报到来了。”
夏丽正闲得无聊呢,看见姐妹们来了。夏丽说:“聪颖,秀儿,英子,洋洋你们咋过来的?一下子都来了。一早起老的小的忙得脚跟不沾地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做头发的呢?洋洋,不是说好了叫上她吗?”
洋洋说:“在外头呢,联系妆婚车的花呢。她们婚庆公司的车在路上坏了,汾水湾那头电话催上了。”
“你还没洗脸吧?”秀儿说:“不落地水呢?”
“问俺芳芳姐哇,”夏丽说:“今儿早起挂在院里枣树格叉上,这天儿冷的,冻了冻璃渣渣啦。噢,你在大厅瞅瞅,是不是挂在衣架上了?”姑娘们把不落地水热了,夏丽仔细地洗了脸。起身前要洗四次呢,取四正之意。窗台上摆着梳妆镜,脂粉、唇红、洗面奶、指甲油,一个白地红花的瓷盘里放着红白喜蛋、龙凤饼。
做头发的是专业艺师。这些年人们手头宽裕了,家家兴攀比,为了一生只有一次的排场都讲究起来,视素日的血汗钱如粪土一般,婚庆公司虽然要价不菲,到了结婚高峰期还是忙不过来。富人装点的是脸面,穷人打肿了脸假装尊严。传统的礼仪,结合现代西方的仪式。雨后春笋般不断翻新的花样,把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的婚礼都包装得富丽堂皇。
为了约会装潢工和代课教师的婚礼,暖洋洋的冬阳照在大街小巷,洒在飘满肉香的院落,穿透贴着红窗花的玻璃窗,把喜气洋溢在洞房里人们的每一张脸上。
顺昌日家里,新郎十二点前打点起身。鹏鹏着一身笔挺的黑西装,藕荷色的保暖内衣配一条胭脂红的缎领带。脚著黑色皮鞋,鞋底贴着箔金剪纸如意图,鞋内垫着别了十字针的龙凤鞋垫。油亮的黑发喷着发胶异彩纷呈,胸前的红花衬着他英俊的身材。今天,四个伴郎的自信都输给了新郎的帅气。
红纱巾苫着儿女双全的荣耀,四个女人在院子里喜滋滋地铺展开龙凤被子。她们分别从四个角向被子中心缝卍字图案。再把双蒂辣椒、红枣、铜钱缝在四角和中间。鹏鹏换上新皮鞋走上女人们为他布置的舞台:杭州织锦龙凤被。踩着红丝线引领的卍字步,鹏鹏的耳朵里仿佛响起刘德华的那首歌——爱你一万年。这首歌此刻是为夏丽唱的。
起身的鼓乐敲打着喜日子的激情,鹏鹏随舅舅走向婚车。
从今天开始,儿子就要交给另一个女人疼爱了,做母亲的有一份失落,更有一份期待和快意。玉琴怀里抱着儿子替换下的旧衣服,手里端着油糕,拥坐在鹏鹏走过的龙凤被里。鹏鹏在车门前照了镜子,咬了红白喜蛋、龙凤饼,开了连心铜锁。玉琴听到车开动了,她独自拥坐的顷刻,眼泪真真切切滚落下来,儿子成人了这是做父母的成绩。
迎亲队伍走了,大姑回到院子里,笑吟吟地对玉琴唱起了戏折子:“嫂嫂,坐甚的咧?”
玉琴回道:“坐福的咧。”
“抱甚的咧?”大姑又问。
“抱宝的咧。”玉琴答。
玉琴用竹筷挟住油糕送到嘴边。大姑见状忙问:“端甚的咧?”
玉琴说:“油糕(又高)。”
这段千古对白演毕,玉琴揉揉发麻的腿站起来。大姑说:“我叠被子,你赶紧回去歇歇罢,一会儿开饭呢。”
顺昌日和村长、弟兄们敬完一轮酒,几十桌下来已有几份醉意。俗语说:三天无大小。时下又兴捉弄公公的游戏,来不及躲,顺昌日的自由也被哥儿文文控制了。
玉琴过去央求:“文哥,放了他罢,他血压高不能喝酒。”
“不喝酒也行,听听说说打好脸子,背了媳妇就行。”
“不要没油水瞎起哄了,他还有好多事要做咧。”玉琴说着就要拖顺昌日走。
“都成你的了,问问你老汉,当初俺儿办时咋种蒺藜来咧?不能走。”
玉琴还要说什么,三牛说:“还有你咧?弟兄们不要叫走了,把昌嫂也打扮起来。”玉琴自知不是对手,这些野男人要是没有法什么不敢做?三十六计走为上。她不屑和这些脱不尽兽性的农人计较,跑了。玉琴躲在街上,不一会,顺昌日也逃出来了。这时,欣欣急急地出来说寻不见红糖放那儿了,玉琴让顺昌日躲在汽车里自己便回屋去寻。
真是冤家路窄,玉琴才走了丈许,就被醉鬼文文迎面撞了个正着。玉琴的心嗵嗵跳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好啊,你老汉咧?这下子逮住你了。跑哇,哈哈,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玉琴被文文一把揪住后领。
玉琴喜也不是恼也不是,她急中生智:“你把俺老汉藏那儿了?快让他出来,焦碳不够了。”玉琴不跑反而边说边往屋里去寻:“文文,快点。把俺老汉藏在那厢了?”
文文堵住玉琴的去路,又醉汹汹地提溜着她往街上走,边走边说:“走你的。不要管我们,顺昌日今日撞在我手里了。走,赶快走。”
玉琴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强压着笑声还得说:“文哥,求求你,快叫顺昌日出来罢。”
文文说:“废话。”农民们总喜欢把这两个字的意思弄反了用。文文站在街们口还不歇心,说:“快走,赶快走。”生怕把顺昌日丢了。
玉琴也怕顺昌日从车里钻出来,节外生枝被文文撞见,忙说:“俺走,走,走得远远的。”文文让哥儿守住街门便自己回去了。
玉琴定睛看时,倒吸一口凉气:车呢?她转过弯给顺昌日打手机,才知道老汉躲在村外了。见了老汉玉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把原委全道出来才缓过口气来,他们像一对患难夫妻坐在车里绕着村子转圈圈,一边用手机遥控着家里的事务,一边等待着迎娶归来的行礼厮见。
话说迎亲的车队浩浩荡荡行进在芦花荡的路上。领头的白色工具车,满载着锣声、鼓声、军乐声和白头偕老的祝愿,彩色的旗帜在乡间路上招展。婚车的前盖装扮着心型玫瑰花团,车身两侧围着粉红鸡毛绒条,后面一溜八辆清一色轿车上,红色气球在左右倒车镜边摇摇晃晃,彩带扎着蝴蝶花儿随风欲飞,个个像扎了两个小辫子的乡下小姑娘,却着一身城市女娃娃的流线型黑色舞蹈衣裤。
头车副驾驶座是掌炮手的专座。逢村过店放几个二踢脚,把喜气一路抛撒着。从汾河湾到芦花荡不过十来里路,当地百姓有句俗语:娶媳妇子绕喜道。即绕远儿走,路线是总管筹划好的,来回不能走重路,取从一而终之意。
车队绕了十几个村子来到芦花荡村东。二留摇下车玻璃点燃喜炮。嗵——啪——,嗵——啪——,嗵——啪——。
来了,来了。”听到村外报喜的消息,石生家里鞭声炮声响成一片,以示接迎。
夏丽梳着高高的发髻,流海从脑门一直垂到齐眉倒向一边。两耳边挂下两缕发胶定型的花卷,耳垂吊着两串镶嵌水钻闪着银光的耳环。喷洒着彩色金屑的柔发里萦绕着紫萝兰的幽香。化妆师细嫩的手指,被洗发水泡得葱白一般,正在给夏丽画眉。听得外面闹纷纷的喜乐声,关门推门声,年青人起哄的调笑声。夏丽抬眼看看窗外,按也按不住的喜色冲破矜持,从嘴角翘起。
塞过几个红包后,门给后生们撞开了。被新郎娶走是新娘迫不及待的愿望,而拒郎于门外不过是女方近似于‘哭嫁’的姿态而已。
新郎一行人围着大厅里摆放着六盘干鲜果品的圆桌,按上下手的顺序坐定,伺茶的女人们把热茶端上来了。
茶后,上席、拆席、赏厨子、新郎拜见亲人。
待女方回赏了打娶灯的伴郎喜烟、喜钱,鼓乐手们把起身的喜乐也吹响了。
礼房先生在麦克风里催道:起身了,新娘赶紧化妆,拿了新郎领带、婚车彩旗的亲朋们把东西拿出来。
芳芳把红丝线交叉架在手指上,象征性地在新娘脸前比划几下,意为绞脸。接着又用黄线、绿线依次剪过,夏丽从此就不是黄毛丫头了。打开男方的拜贴盒子:五色线挂在衣襟上,金银顶针装在衣袋里,针别在鞋垫下,瓦金笔架缝在脖子后面领子上。化妆谢礼和儿童钱分发给了女眷和孩子们。
领了喜烟的人们把从新郎那儿哄抢来的物件一一交出。
夏丽穿好婚纱,咬一口红白喜蛋,再咬一口龙凤饼,表哥抱着夏丽走出街门,夏丽把插着四玫硬币的喜馍馍攥碎了抛给孩子们。表哥抱着新娘送上了婚车。取意:哥哥抱妹妹,好活一辈辈。
彩旗威风凛凛重新招展,铿锵的锣鼓、雄洪的军乐、嗵啪的喜炮一路敲打着路经村庄的空寂和无聊,招唤着喜欢凑热闹人们的笑脸和新人的幸福。乐手们用冻得发僵、舞得发麻的手臂为这一对新人拥抱着腊月里的春天。
回到汾水湾更加热烈的开门红,更加密集的礼炮声和着鼓乐狂欢的兴致,托起一个个潮头姿意冲撞着人们的耳膜。把腊月十六的黄昏彻底煮沸了。
车在村口拱门前停了。新郎背着新娘众星捧月似的,在伴娘和伴郎的簇拥中,此起彼伏的调笑中,不依不饶的捉弄中,艰难地移动着。男孩子们挤挤挨挨,姑娘们推推搡搡,迎新的女人们插不上手,只能跟着走走停停、进进退退。只是苦了鹏鹏两条不堪重负的腿。
究竟是逃不过的。亲人厮见怎么能缺了父亲母亲。玉琴先回来探听消息,尽管绒线帽捂着脑瓜,围巾缠了大半个脸,还是让三牛媳妇认出了走式。找乐子的婆姨们俘服了她们的猎物,嘻嘻哈哈给玉琴抹了红脸蛋,头上用红头绳扎了三个牛角辫,把早以备好的古装让她穿了。待新人被男女宾客挤至门前,玉琴一手提铜锣一手持锣锤,迎出门来。她照着三牛婆姨教的话,一边敲锣一边问儿子:“狗狗给妈妈娶回媳妇来啦?”
男孩子们拥着鹏鹏和夏丽。一个小伙子催道:“说。”
鹏鹏两腿打颤,喘着粗气说:“说什么?”一个小伙说:“记心呢?欠揍呀?你。”他说着举起了皮裤带。
鹏鹏赶紧说:“我说,我说。妈妈,亲牛牛给你把媳妇娶回来了。”
玉琴说:“狗狗亲蛋蛋。俺孩儿回来哇。”婆姨们笑得前仰后合。
姑娘婆姨们趁小伙子们不防备,一齐用力拥着鹏鹏往前走。此时,鹏鹏的腿已不属于自己。鹏鹏仿佛是载着新娘的独轮车,摇摇晃晃被众女人推进洞房。
红烛在洞房的四角燃着家的温馨。窗台上一个瓷盘里,糕面捏的高小子欢喜地抱着一盏豆油灯。夏丽用过红糖水,稍事休息,伴娘照护她拜天地、见父母。
新人进了家门,顺昌日才小偷一样潜回来。然而,他的哥儿们个个是便衣侦探,不露面便罢,一露脸儿准没得逃。顺昌日被画了大花脸。
文文说:“背媳妇让你逃脱了,算你有本事。叩头厮见时最好听说些儿,不听说的话,可是不要怪哥们叫你下不来台昂?”他转身和大家说:“大伙儿听着,我文文说甚是甚,昌哥再不给咱面子,咱们不捧场了,立马走人。”
老弟兄们笑着起哄:“是。”
顺昌日的大花脸在灯光下和着汗水油汪汪地放着光,顺昌日脖子上吊着酒瓶子,胸前佩着大纸牌,成了这一场婚礼最亮丽的道具。厮见开始了,天地爷神位前摆了一条长凳,顺昌日坐在左边,玉琴坐在右手。
鹏鹏和夏丽一起说:“爸爸,俺给你行礼了。”顺昌日赶紧应诺。
文文说:“不行,重来。”他给了夏丽一个空酒杯杯,他从顺昌日酒瓶里斟满酒,端给夏丽,:“新媳妇,你说,爸爸,喝咱的一盅酒哇。”
夏丽羞红了脸,说:“就这罢,俺不会说。”
文文不依。玉琴说:“行了,拜过了。”说着站起身欲走。
文文说:“嫂子是不给面子了?”他催:“新媳妇,快说。”
玉琴忙说:“俺孩子没啦听清楚,你说甚来咧?”
文文清了清嗓子:“听清了昂。”他对着顺昌日高声道:“爸爸!喝咱的……”文文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只见玉琴捂着嘴,人们的笑声像撞开炒锅的爆米花,哄的一下爆发出来。要逗乐子捉弄新媳妇,反叫玉琴耍了,文文的花样没了灵感。他瞪了玉琴一眼,自嘲而滑稽地做个鬼脸说:“攒的哇。”
吃了合婚席,新人入了洞房。
厨房贴灶的珍大娘端着一碗拌结汤笑嘻嘻地进来了。她对起哄的小子们说:“你们不要急着闹洞房,先让新人吃了拌结。”她对夏丽说:“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知道了吧?”夏丽笑着点点头。
珍大娘说:“荤厨房,面厨房,清汤利水做了一碗拌结汤。”她把一块拌结用竹筷挟到夏丽嘴边,让她咬在嘴里。面里包着辣椒面,炝得夏丽直掉眼泪。
珍大娘笑了,说:“吐出来罢。”她让新娘把拌结压在床垫一角。
她又搅一搅汤:“葱花花,油点点,胡椒面面姜片片。”夏丽再咬过拌结,把它压在床垫另一角。
珍大娘搅着香喷喷的拌结汤,边搅边说:“东搅西搅,儿女不少。南搅北搅,过了年生个胖小。”
夏丽依次把拌结压在床垫四个角下。珍大娘撤下了汤碗。她唤过欣欣交待了一番话。
一会儿,小姑子欣欣提着新人的大红塑料尿盆进了洞房,盆里蒙着鱼鱼兔兔小花馍。欣欣娇羞地边走边背诵祖宗留传的戏词儿:“姑姑提盆盆……”
夏丽接上说:“儿女一群群。”说着,夏丽一拳把糊盆子的水红纸捅破了。小子们踮着脚取下柜顶上的儿女盔盔来,儿女盔盔也装着鱼鱼兔兔,蒙着水红纸,纸面也贴着大红如意剪纸。
欣欣接过盔盔端给夏丽说:“姑姑端盔盔……”夏丽接过来说:“儿女一堆堆。”说完,夏丽又戳破封口。
闹洞房是年轻人的事,表嫂取下柜顶上婚礼仪式最后一件道具——苕帚。她铺了床,扫了褥子,把一天的忙碌交给了寂静的夜,也把久久渴盼的新婚良辰交给了鹏鹏和夏丽。
古时候,老百姓读不起书,不识字,所以,人们无法用文字传授性知识。既然‘性’在愚昧的文化背景下,无端蒙羞几千年,遮遮掩掩被老祖宗所不齿。在人们不得不传宗接代时,只能发明花样百出的隐语,鼓捣林林总总的图腾,含蓄地启迪新人的性觉醒了。
“聊事日”是第二天的重头戏。石生看过夏丽一切顺利。用了早餐,叮嘱亲家几句日后要担待姑娘不懂事的言语,这一场婚礼到此圆满结束了。
(完)
平遥本土文学:汾河在这里转了一道湾(一)!
平遥本土文学:汾河在这里转了一道湾(二)!
平遥本土文学:汾河在这里转了一道湾(三)!
傍晚,饮一杯清茶,读赵静诗文选二篇!
光影定格的人生,从50年代到90年代,一个平遥普通家庭的老照片。
平遥本土女诗人彩英作品:桃之夭夭。讲述桃花林里壮美的心情故事!
平遥农村记忆:黄仓的石板.
清末平遥著述第一人—张桂林!99.99%的平遥家居然都不知道!
赵静:一个平遥人的台湾纪行,走近同根同族却与我们不一样的台湾风情!
一首歌里悲惨的记忆:光绪三年闹年成歌,字字都是山西人的血和泪!
讲述你不知道的平遥历史
讲述你不知道的平遥人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yuncaibanjia.com/fjcf/75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