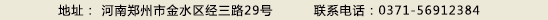葵花岁瓣middot梳头
葵花岗水库对岸,是绵绵不绝的山丘。
晨曦勾勒出山脊,像孩子练习簿上生涩的波浪号,高一笔低一笔,紧紧张张。
终于画顺溜了,却不小心突兀出一笔硕大的浑圆,滑溜溜的。那是葵花岗最高的山脉,无名。
日头破云而出,好不容易拱上这个无名山顶,却总叫人担忧,它会顺着滑溜的弧线滚到水库里去么?
我就这样坐在小板凳上杞人忧天着。
在我身旁,是许多个板凳,高高低低,摆成一排。女孩子们坐在板凳上,等着各自的娘梳头。
只要天晴,葵花岗清晨的第一幕,一定是梳头。
丫头多的,做娘的会心烦,一边梳一边数落:憨人一把尾啊,只晓得长头发!
便是这样,也未见哪个娘狠狠心,把女儿的辫子给剪掉了。
那会儿,小女孩都渴望有一头长发,可以编出长辫子
芳芳娘嘴里叼着一根橡皮筋,手里捏着一把马尾,收拢收拢,就要扎上了,却听芳芳一声惊叫,正啃着馒头的她,把舌头咬了。
她娘偏过头去要看她的舌头,她便乘势哭了起来。一团馒头在口里,吞也不是,吐也不是。
她爹突然一声吼:叫你吃东西别唱歌,唱唱唱,又把舌头咬了!
芳芳的哭声戛然而止,她奇怕她爹。
芳芳娘直起身来,狠狠地盯着她爹,咬牙切齿地蹦出三个字:娘西皮!
芳芳爹讪笑着安静了,他奇怕她娘。
不知谁的娘,及时岔出笑话来:芳芳,赶紧叫你娘去割肉,牙齿想吃肉了!
芳芳爹找个台阶下了:我们芳芳门牙都掉了,怎么吃!
姐突然从板凳上跳下来,跑去看芳芳的牙,一板一眼地说:芳!下面掉的牙齿,要扔屋顶上去哟!
这是规矩,不知谁定的,我们都严格恪守:下面掉牙扔屋顶,上面掉牙扔床底。否则,就别想长出牙齿来。
据说这牙齿,还只能扔在自家的屋顶上,扔谁家谁多长牙。
姐常指着电影里的龅牙对我说:看看看!谁把牙齿扔他们家屋顶了!
我问:长了龅牙怎么办?
姐说:那只能被坏人抓去当汉奸了,汉奸都是龅牙!
这事儿太严重了,我们得防范。
电影《小兵张嘎》里的汉奸翻译官,就是大龅牙。
有一段时间,我和姐恨不得爬到屋顶上去,把每一块瓦片搜搜干净,看有没有扔错的牙齿。突然雷声咋起,大雨滂沱,姐欢喜地跳起来:妹!大雨把瓦片都冲干净了,肯定没有牙齿了!
芳芳的马尾巴梳好了,头上顶着一朵火红的丝绢,穿着红裙子,像一柱燃烧的喜烛。
喜烛的眼泪干了,从口袋里掏出牙齿递给她娘:给我扔到屋顶去吧!
芳芳娘将牙齿递给她爹:别太大劲,扔出去了!
芳芳爹偏着身子,胳膊一扫,牙齿上了天。
不知谁叫了一声:扔在王晓东的屋顶上了!
王晓东捏着馒头跑了出来,看了看屋顶,淡定地说:我的牙换完了。
芳芳哭兮兮地看着她娘,她娘狠狠地盯着她爹。
掉牙的习俗,下面的牙齿得扔到屋顶上
艾东娘端出木盆,打水洗衣服:芳芳,不长牙多好啊,风吹一吹,凉快!
姐突然想起来:芳芳,牙齿掉了,千万莫用舌头舔,舔了也不长的!
我紧张地举起镜子看我的缺巴齿,我整天舔牙床。
还没看清,脸就从镜子里拉了出去。娘掰过我的脑袋,开始给我梳头。
我叫着:为什么不先给姐姐梳!
娘没好气:给她梳,你又溜吧?
昨天,昨天的昨天,我都没有梳头。
都是趁娘给姐梳头的时候,我拖着书包偷偷跑了。
暑期,太阳下满处跑,头上长满了痱子,娘给我剪了短发。开学后,头发老也长不出来,只能扎许多的小辫子,一朵一朵,头上开满了喇叭花。
便是这种极简单的喇叭花,娘也生怕我玩散了簧,总是紧绑紧扎,牢牢实实。所以,每每辫子扎完,我的一双眼皮便高高提起,像二郎神眉心中间的那只眼,几乎可以竖着看了。
由此可以想见,梳头对于我来说,真像一种体罚。
娘出手重,偏偏不承认,一梳子下去,我便开始叫唤。娘总能找到理由:三天不梳头,梳得眼泪流!
我挣脱了娘的手就往外面跑,平房再起笑声。
娘和姐两头夹击,像老鹰抓小鸡,将我揪了回来,按在小板凳上。娘两腿将我紧紧夹住,我接着叫唤,娘便接着吆喝:三天不梳头,梳得眼泪流!
姐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每扎一个小辫儿,她就在一旁数一次: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放屁就是它!
反正,我头上的喇叭,总有一朵是拿来放屁的。
爹的水墨画,说我小时候的头发就是这种小喇叭
爹的水墨画。娘给我头上扎满了橡皮筋,其实非常疼。
姐正数着,艾东娘凑了近来:英儿,阿姨给你梳个好头!
艾东娘养了三个儿子,一早女孩子们梳头,她便只能洗衣裳。三个儿子不适时宜地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她便突然生气:晃什么晃!你们三个,把一个是个丫头也好!
艾东娘总说,我生三个做什么?还不是以为可以生个丫头!
实在心里欠得慌,便扯着姐到她家门口坐着,镜子、梳子、头油、发卡,整齐地摆在一旁,跟开发廊似的。
一边梳一边跟姐说笑,温暖地像春天,能生出瞌睡来。
梳罢,上了头油,举着镜子给姐照前照后:英儿几漂亮,头发也顺!
我怕娘梳头,总盼着艾东娘哪一天把我叫过去。可她便是百无聊赖,也一定不会招惹我:只有个静儿,碰不得挨不得,青喊八叫,真烦人!
艾东娘说的极是,娘也终于烦了。
那会儿,娘在养猪场工作,有一段时间,好几头老母猪生娃,娘和同事们天天守夜,着实累了,顾及不了我,便开始由着我自己折腾。
我的头发我做主,自我收拾,有人起点高,有人起点低,我,貌似没有起点。
记忆最深刻的,一定是寒冬里梳头。
出了被窝,就是棉袄,胳膊挤在厚厚的棉花里,直直的,像两管猎枪,根本没法转弯。梳头,就成了老大难。
大女孩是披着棉袄梳头的。一头秀发,左偏偏,右偏偏,十指绕花,一会儿编出两股水灵灵的辫子来,一对蝴蝶结扎在末端,风里扑扑落落地飞着,真美!
我爱欣赏,但不爱收拾。怕冷,又怕疼。
早晨醒来,摸摸后脑勺,橡皮筋还在头发上栓着,便急匆匆地抓着风雪帽往头上一套,从早到晚不摘下来,谁也不知道我这闷葫芦里装的是什么。
七十年代流行的风雪帽,大多是买的,帽子末端,是两条长长的毛线带子。
哪天娘和姐实在看不过眼,给强行梳了一次头,也总能管上好几天。
其实,芳芳跟我差不多,也总是乱发飞度,像一团黑色的疑云,走哪儿都让人有思考的欲望:她俩,是有娘呢?还是没娘?
记得芳芳常高兴地对我说:静儿,你妈发现么?我妈又没发现,以为我梳头了!
我们到底是女孩子,总归是爱美的。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放学路上,风雪帽终于戴不住了,只好摘下来,挂在脖子上。
斜阳夕照,人影在石子路上被拉长,突然有长大了的感觉。
两条风雪帽带子,好似修长的辫子,左甩右甩,风情万种。
天啊!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写照?
大了,大了!我们拔苗助长了。
大了是要骑自行车上班的,是要做新娘子的,是要漂亮的。所以,梳头发吧!
爱美之心突然爆炸了,山崩地裂!我重生一般从石头缝里蹦了出来,无师自通地开始臭美。
七十年代,女孩子们头上常年顶着各色蝴蝶结,像春天的花儿。
我有一股妙手生花,一鸣惊人,脱尘抛俗的欲望:一定要梳出全世界最惊艳的头发!
颜色,对,第一步是颜色。一定要让头上万紫千红。
蝴蝶结?不够。发卡?还是不够。手里不是有剪刀么?家里什么东西漂亮亮,剪什么!剪掉枕套上盛开的牡丹花,扎在头上!
娘洗了枕套,就晾在门口的绳子上。我拿着剪刀,东一下,西一下,挖出几个大洞洞,带着绿叶的牡丹,就开放在我和芳芳的头顶上了。
晚上娘套枕头,满面惊讶:这不是老鼠啃的呀!
那是娘结婚时托人在上海买回来的刺绣枕套,算是家里最精美的东西了,平日里都舍不得用,在我手里彻底报废。
一根枝条,杀气冲冲地捏在娘手里,我被压在搓衣板上,第一次发现哭不出来,真有一种为了真理可以不怕打的情怀。
芳芳将牡丹花还了过来,手背被他爹打出了红杠杠,她居然也没有哭。
这真是一个笑话,从前娘要为我梳头,我东躲西藏。如今我积极梳头,娘却开始了梦魇一样的日子。
因为梳头,我曾摔碎过许多镜子。
周末,芳芳从口袋里掏出两朵塑料腊梅花,那是她家小盆景上的。她弄了一根毛线,将腊梅花窜起来:静儿,扎头上好看!
此地无银三百两,腊梅堆在头上,怎能不被家长逮着?
晚上,芳芳爹怒气冲冲,不是为她扯了花儿,而是因为她撒谎:我没扯,我捡的!
爱美之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挨了打,站起来,立即去照镜子:蝴蝶结,花手帕,塑料发圈,各色发卡,只要能堆在头上,就一个都不落下。
每每梳完头发,走出门,总能听见人惊讶地问:啊呀!静儿,你这脑袋顶得起么?好几斤重吧!
其实,这几斤的灿烂,也不过是豆腐渣工程。待疯赶打闹,头发四散,漂亮的头饰通通失落。
那会儿,进城买头饰很不容易,也颇为破费,娘实在被我丢恼火了,就扔给我两根红毛线:三文不当二文,好东西在你手里只能管一下!
我翻着白眼,不高兴。姐指着墙上红灯记的年画说:妹!红毛线好,跟铁梅一样!
没过几天,红头绳又丢了。
娘不耐烦地扔给我两根橡皮筋:再丢,就把头发剪掉!
橡皮筋还是弄丢了,早上一对辫子出门,晚上披头散发回家。
记得娘气咻咻地对爹说:你的丫头在外面撒大麦!什么东西都能撒!
娘是决计不管我了。
一大早起床,蓬乱着头发,我实在没东西扎头发了。
娘一句话不说,甩门出去了。
我开始仰着脖子干哭,姐把她的一对辫子变成一股,匀了一根橡皮筋给我。我拿在手上,生气地一拉,断了。姐头也不回,背着书包走了。
爹总能想到办法,在缝纫机抽屉里找出娘做内裤的松紧带,剪一截,递给我:这个东西也能扎!
松紧带还真扎不牢实,没到学校,就不知丢哪儿了。
记得那是个雨季,爹许多天没出车了,他也就没时间给我买皮筋。
一早起床,我顶着一头乱发,望着爹叫唤:没人管我啦!
爹从容地从工具包里抽出半截子自行车内圈,拿着剪刀咔嚓两下,剪了好几个红环环,照样扎起来了!哎嗨哟,扎呀扎起来!
自行车圈内胎
自行车内胎剪成的橡皮筋,弹性不太好,容易断。
扎吧扎吧,好不容易手脚娴熟了,头上突然长了虱子。
娘发现我老在头上挠,神色紧张地扒开一看,惊地大叫:啊呀!我静儿头上长虱子了!
一声晴天霹雳,左右邻居,人人都觉得自己头上痒了起来。
芳芳娘慌慌张张跑来:我家芳芳也长虱子了!怎么办?
娘是养猪的,当然知道怎么办:用敌百虫杀!
敌百虫,是毒药,专门给牲畜杀跳蚤虱子的。
用量多少?娘的作风,多多益善!有时感慨,我能活到今天,真是幸运。
一早,娘烧了水,给我把头发打湿了,便一层层地涂抹敌百虫粉剂,臭烘烘的,真难闻。涂完了,再用毛巾将我的脑袋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好:坐在外面,不要进屋,怕半死的虱子掉在家里又活了!
烈日下,我和芳芳俩在门口晃来晃去,像两兜包菜,种了一上午。
芳芳一口咬定,是我将虱子传给了她。
我倒是认准了,是她将虱子传给我的。
其实,那会儿在农村念小学,总有乡下小姑娘长虱子,这个小东西,东跳西跳,跳到我们头上也很正常。
虱子是灭掉了,痒的感觉还在持续。有事没事,我总要在头上挠挠,娘说,看见我挠,她就周身发痒,难受极了。
晚间,娘和芳芳娘商量:把她俩送去烫头吧!若还有没死的虱子,就把它们电死吧!
我和芳芳听见,欢喜地蹦了起来。
那会儿刚刚时兴烫发,那种摩登还没来得及普及在葵花岗的成人世界里,竟率先降落在我们头上了,简直是因祸得福。消息传出来,天天避着我的姐羡慕得不得了:早晓得,我也长个虱子就好了!
烫发的日子定在下个周末:让静儿爸带她俩去!
下个周末,像一个无底洞,可以一直下下去。下个周末到了,还有下一个。娘总归没说错,下一个嘛。
原本我们已经忘记了,但是葵花岗是一个具有团购意识的群体,烫发比虱子传染得快,几乎所有女人都决定要去烫发了,下周就变成了明天。
八十年代初,一到周末,理发店里就挤满了烫发的女人。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让直发变弯了,越弯越好!
明天,我就和芳芳进城去烫头发了!
夜里,睡不着,从床头翻到床尾,问姐:你说我会不会像个女特务啊!
其实,我就想当个女特务,我觉得特美。刘胡兰,女英雄,还是留给别人去当吧!
第二天一早,爹的车就停到门口,我和芳芳像猴子一般窜到车上。
许多的女人们都来了,不论老少,她们都要进城烫头。迅速,车上挤满了人,来晚了的,站的地儿都没有。
通常都是这样,只要遇着人多,娘总是一个字:让。
她生怕人说咱们家搞特殊化。所以,我,就被娘从车上扯了下来。
芳芳喜滋滋地看着我:静儿!下午我回来,就是弯弯头发了!
我憋屈地难受,无数个下周,终于来了,却成了泡影。和娘纠缠无果,便直接滚在地上,大哭大闹。
车上的人望着我,像看戏一般:哎呀,静儿,这么漂亮的衣服滚成灰老鼠了!
娘将我从地上拉起来:今天我给你烫头!保准比芳芳烫的好看!
娘烫头,就是一把火钳,插在煤炭炉子里,烧得火红,立即在水桶里淬火,乘着温度高,扯出我的一缕刘海,在火钳上绕几圈。一阵焦糊的味道飘过,抽出火钳,额前便是一圈螺丝环。
几次三番,我的头上堆出了一捧黑麻花。
火钳烫头法:先把火钳烧红
火钳烫头法:过水后开始在头上绕圈圈
娘递给我镜子:看看!比芳芳好看多了!她今天肯定没你弯!
我跑出门外,等过路的人惊讶地问我:呀,静儿烫头了!
没有人,对头发感兴趣的人全都进城烫发去了。
几阵风吹来,火钳烫的头发很快就直了,我便继续哭。
哭到晚上,爹的车终于回来了。一车人哗啦啦跳了下来,落了一地的闲言碎语:哎呀,烫什么头啊!好多人排队,我们挤都挤不进去!
哎呀,好贵啊,两块五,要买个洗脸盆了!
哎呀,哪里好看撒,像不梳头的,鸡窝一个!
哎呀,烫头要坐好几个小时,冯师傅的车等不来的!
哎呀声中,芳芳出现了,在她娘的怀里,睡着了。
爹说:烫发店的人太多了,要叫号,芳芳娘不想等,芳芳就在大马路上打滚,嚎啕大哭。最后,头没烫,屁股还挨了她爹几巴掌。
第二天一早,我和芳芳站在屋檐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她说:静儿,以后我长大了,结婚了,就烫头去!
恰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头发没烫成,那就继续在发型上做文章。
电视剧《敌营十八年》热播,一阵风,盘发开始流行。
那会儿,没有定型发胶,没有电吹风。一堆黑发卡,横插竖插,终于在头上搭了个雀巢,貌似盘发。可风一吹,便蓬松松的,不敢低头,稍微一动,绝对散簧。
盘发没维持几天,《霍元甲》又开始热播,顶在头上的鸟巢,立即散下来,被编成“秀芝”发型。
半圈蜈蚣,从左边爬到右边,顺着耳朵散成马尾巴。脖子一扭,马尾巴能甩死好几只蚊子。
一时间,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全是大大小小的“秀芝”头。
“秀芝”正待发扬光大,《血疑》开始了:哇哒西路,谁衣哪呀,由路西得……
于是,山口百惠的假小子头迅速风靡,一只只蜈蚣一夜之间被消灭干净,满城尽是假小子!
是长是短,是留是剪,长不停的头发,从幼年到少年,是一团开不败的花。
最怀念,葵花岗平房门口,那一排高高低低的板凳。像钢琴上起伏的琴键,演奏着一曲爱美的歌。
余音绕梁。
Silence
转载请注明:http://www.yuncaibanjia.com/fjzl/96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