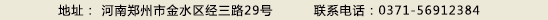江雨薇天堂寨,我的天堂上
01
黄尘捂着被老婆用小板凳头砸中的脑门,狼狈地夺门而逃,瞅老婆没有追着他打的意思,耿着脖子冲老婆吼:“我就要回天堂寨!”“他妈的!杭州这么赚钱的地方你不待,回天堂寨,回天堂寨,你回去行(找)魂啊?你要是再敢丢下这里的生意,回老家瞎折腾,我们就离婚!什么回乡创业帮扶脱贫?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呀?你敢跨出这道门槛,就永远败(别)回来啦!”老婆机关枪样的咆哮声,撕裂寂静的楼道,像龙卷风在背后撵着他跑得更快。
亲戚们常嘲笑年过半百的黄尘,老婆一声吼,就吓得屁滚尿流,白长一副五大三粗的身板,三脚都跺不出个响屁,就是一块任老婆宰割的肉头。敦实憨厚的黄尘不这么认为,二十多年前的安徽农村,可谓穷山恶水,自家兄弟多,日子过得寒味(凄荒)。春荒季节,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屁股打板凳响(形容穷得没有衣服穿)。自己二十多岁了,也娶不上媳妇,搁如今说法就是大龄剩男了。
那个年代山里普遍都穷,有姑娘的人家都希望女儿嫁到大山外,老婆的父母也不例外。老婆和黄尘同住一个庄子,她娘家姐妹们多,家里没有得力的男劳力。黄尘见老婆像个男孩子样,干田间地头的活,心生同情,常常默默她一把,一来二往,日久生情。只可惜黄尘家出不起彩礼钱,一直不敢上门提亲。
那年,老婆娘家急需钱,给她家唯一的男孩子上大学。老婆以死相逼,顶住父母的反对和打骂,啥彩礼也不要,只要黄尘借钱替哥哥付学费,她就嫁给黄尘,愿意和他一起吃苦还账,
黄尘觉得自己娶到浓眉大眼这么漂亮的老婆,还比自己小好几岁,是自己的福气。若不是河东狮吼的老婆,比自己还能吃苦耐劳,自己一个来自天堂寨的农民,咋能在杭州买房安家、成立公司?老婆脾气火爆没文化怎么了?自己就喜欢她这种直来直去的炮仗性子,啥事噼里啪啦炸一通,明白敞亮!
走出小区,天都铁塔霓虹闪烁,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不知疲惫地蹦踏着。黄尘就站在那里看,看着看着,他就觉出了自己的孤独,很深的孤独。在这个城市,他虽然有房有车有公司,手下还有几十名员工,别人总是一口一个黄总叫着,看起来很风光,其实他觉得这些都不是他内心想要的生活。
曾经的他以为自己拼尽全力,让生活在城市开出绚烂的花朵,就会快乐。如今在他人认为最是热闹最值得开心的时候,他往往却陷入深深的孤独、恐惧和彷徨之中。虽然两地他都有房子,他却时常感到内心空荡荡地。一颗心蓬转惊悸无处安放,好像当年他人走出了天堂寨,魂却丢在了那里,虽然曾经贫穷的生活是那样令人不忍回眸。
老婆生气,骂他,打他,他都不怪她,这些年他曾两次回乡创业,由于市场预估不准和天灾,赔掉了近百万。现在刚有些积蓄,他又想再次回天堂寨,流转闲置的土地,投资兴建茶厂,也难怪老婆不同意。城市的繁华与喧闹不属于他,他不相信空旷的山野,也难容下他过上幸福生活的欲望。绕过跳广场舞的人群,黄尘走向不远处以法兰西文化为基调的天都公园。
黄尘摸出一支烟,嗅一嗅,烟在粗糙的指尖反复旋转,然后习惯性地把烟屁股在大拇指甲盖上跺一跺,直到烟头空出一小段,这时候烟丝更加紧实了,再点燃。他狠劲地猛吸一口,烟丝快速燃烧,发出细微的声响,贪婪地吞吐一阵后,他的表情渐渐苏活。
在烟雾里,黄尘目光虚视,叠泉池中太阳神、小天使、阿波罗战车、海妖、怪鱼这些被城里人说成是艺术品的铜疙瘩,怎么看也不如老家山上郁郁葱葱的毛竹,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和绿油油的茶树好看。
天堂寨是植物的王国,动物的天堂。春天,鸟儿比人醒的早。推开窗,空气特别清新,远处的山,层峦叠嶂,连绵起伏,云蒸霞蔚。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肆意怒放,不管不顾地张扬着它们的美,一路逶迤,染红山麓。
山涧溪水淙流,山坳里有袅袅的炊烟,从泥胚老屋的上空慢慢升腾,缓缓消散,与朝阳遥相呼应,远远眺望,如诗如画。
悬崖上,映山红点缀于绿树翠竹间,娇俏妩媚。绿崖之间,瀑布跌宕飞泻,声如钟罄。面对如此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一瞬间,仿佛置身人间仙境。那种感觉即使生活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城市,也是体会不到的。
作为一个高考只差几分而落榜的农民,黄尘内心总有些挥之不去的文艺情怀。离开天堂寨二十多年了,他总在怀念记忆中的乡村。他怀念的并不是完整的过去,记忆有自动美颜功能,自动屏蔽掉过去乡村的本质是贫穷、清苦和饥饿。他时常被自己美化了的回忆所打动,激发他要回天堂寨的冲动。
往年这个季节,黄尘就牵挂着山坳里的那几亩田,担心奶奶累坏了,总要抽空回老家帮奶奶把秧插了。爷爷去世多年,多次劝年近百岁的奶奶,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粮食,不要种了。山上的茶叶也不要采了,手工采茶、炒制,太辛苦太麻烦,想喝茶,买一点。
奶奶总是说,家门口这么好的田,能种一点是一点,不种荒着,太可惜了。买的茶叶,哪有自己制作的手工茶好喝养人?俺们这些山里人,个个精神头都十足,而且长寿,这是山神眷顾俺们这些凡人。干活干活,人不干了,咋活?人活着,若是不干活,还有啥意思和奔(bèn)头(希望)?
天堂寨有许多像奶奶一样的老人,他们不愿弃山进城,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对大山的深情,对劳动的执着,常常让黄尘心生敬畏,也让黄尘更深层次地理解了,愚公为什么要子子孙孙的移山,而不搬家。
前阵子,回家做清明,黄尘站在坡上看庄前的那几十亩良田,只有一块奶奶和小姥去年还在种的田里关着水,剩下的全都长满了杂草。曾经的当家塘,塘底显现厚厚一层褐色的树叶,几乎看不见水,心中不免痛惜。
以前,村民组把水田分为上中下三等,三年一换。每到抓阄分田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够抓到庄子前的那一片上等田。田旁边有水塘,两侧有低山,不怕旱,不愁肥,也不怕风,抓到庄前的田,也就意味着三年旱涝保收。如今老一辈的相继离世,中壮年外出打工,年轻一代的根本没人会种田,也没人在意自家田的位置在哪,农田也不再重新划分了。
黄尘这一代中年人大多在庄子上盖了楼,也有不少人,还在所谓的城里也买了房子,人员遍布江浙广、北上深和省城合肥,最孬熊(差)也在县城有了自己的家。
虽已阳春三月,无论是田地,还是山坡沟壑,依旧荒草蔓蔓。奶奶去世前点的一小片地里,有油菜花寂寥地绽放着。没有被祭扫的祖坟全都淹没在半人高的荒草中,如果没有隐约矗立着的墓碑,几乎无人知晓哪里深埋着先人的遗骸。
远远地看不见上坟的人,只见袅袅烟雾四起,零星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直冲云霄的烟花,声声震耳。空旷处散落着一些已培上了新土的坟茔,并插上了叫作是“坟茔吊子(或帽子)”的彩色剪纸。风一吹,挂在竹枝头招摇的彩纸拉花,冷清又寂寞地响着,醒目地告诉人们,这家祖坟还有晚辈,儿孙们已回来上过坟了。
清明几处有新烟,满坡哀思与尘埃。黄尘放眼远山,苍凉在空静里回荡。
清明,只有清明,大伙都怕别人戳脊梁骨,妄议这家祖坟是绝户头,才不得不回乡,在祖坟上添一锹新土。黄尘正在心底感慨: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不远处的土坡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响声,随风滚动。
黄尘惊异地望过去,风卷着纸钱的灰片和烧黑的草沫,落在他的头发和衣服上,噼里啪啦的响声,由一股股黑烟变成明晃晃的火球,吞噬着大片大片的荒草,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
黄尘愣神的一会儿功夫,火球蔓延成一片火海。等他醒悟是坡上祭祖的人家,等不及纸钱全部化为灰烬,就急匆匆地点燃烟花炮仗,磕完头,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绝尘而去。
火借风势,一场火灾已酿成。坡下田地里的荒草已全部烧焦,黢黑一片。火势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着他所站的位置席卷而来。
眼看着火即将翻过山岭,抵达村庄。附近养鸡场年轻的小老板,隔老远冲着黄尘喊:“我打怎么是空号?”“那你打吧!有事找警察总没错!”黄尘不假思索地让对方报警。话音落地半晌,黄尘恍然,火警电话不是吗?小伙子怎么打呢?难不成国外影片看多了?
闻讯赶来的警察,他们手里的灭火器在大火面前,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幸好风停了,火势在灭火器的控制下最终偃旗息鼓。望着慢慢散去的黑烟,那些淹没在荒草深处的坟茔堆显现出来,就像是刚看了一部关于情怀和青春的电影,一个时代的绚烂和斑驳倒映在黄尘的眼中。望着警车远去,黄尘忽然发现自己曾经那么讨厌的警察,形象忽然高大起来,不由自主在心底祝他们永远平安!
黄尘坐在爷爷奶奶的坟前,又点燃一支烟。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02
九十年代,黄尘抱着刚出世的儿子,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终于有儿子啦!就算是被罚款也值啦!他望着窗外,欣慰地想着。一阵阵热风送进窗外野生五角花(紫茉莉)的馨香,他的心突然又感到十分地沉重,怄愁焦灼的感觉从背后缓缓升起。
女儿才三岁,在农村,第一个女孩未满五岁,偷生二孩,算超生,被罚款两万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人民的收入逐步提高,万元户的说法已演化成: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但在那个深受传统观念影响,思想还不够解放的年代,1斤粮食卖2角多钱,村干部月工资才四五十元,真正的万元户并不多。两万元,对于山里的农民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黄尘靠着门框,一连扔掉十几个吸得很残的烟头。他眼巴巴地瞅一眼妻子,再瞅一眼孩子,人在烟雾里,也在愁苦里。愁眉不展,一声叹息,一声无奈。
为了尽早凑齐罚款,黄尘背着铺盖,拎着行李踏上打工之路。第一次出远门,黄尘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更不清楚到了外面,自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山和土地能靠什么赚钱。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首都北京是黄尘从小就向往的地方。“我先去北京探探路子吧,如果能稳定下来,明年春天,我带你去天安门,看升国旗。”黄尘把老婆递给自己的零钱揣进衣兜,脱掉鞋把四张百元钞票分别藏在双脚的鞋垫下面。
愣头愣脑的黄尘终于踏上向往已久的地方,拘谨地路都不知咋走了,眼神怯怯的。晕头转向,东张西望之际,迎面而过的人,冷不防地从两侧把他抓住,同时有人在他后腿弯子处猛踢一脚。他不由自主地跪下,被反剪双手按倒在地,恍惚中,他嘴里发出一声惨叫。正想抬头,一副冰冷刺骨的手铐卡在他的黑黢黢的手腕上,两钢圈之间有一链条连着,他一挣扎,那链条就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那种只有在电视里才看过,警察抓坏人用的手铐,扣在自己的手上,黄尘感到从没有过的委屈和屈辱。那经历,每次回忆都是扎在黄尘心头的一根刺。
辅警抓住他的胳膊往上一提“起来,走!”这时,黄尘才看清逮住他的是两位身穿制服的人,他们宽宽的人造革腰带上挂着黑色的电棍,没等他开口,不由分说:“外国友人访华期间,严禁各地上访人员在京流窜,走!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辅警没收了他口袋里的身份证和零钱。
那咬住黄尘手腕的手铐,有一股彻头彻尾的寒气,凝固着他的血液,使他头脑清醒过来。他运动僵硬的舌头,直着嗓子嚎叫着替自己申辩:“警察同志!我不是上访的!我也没干坏事!你们抓错人啦!”辅警从两边架着他的胳肢窝,拖拽着把他塞进警车。不知道过了多久,黄尘被带到一处屋子里。辅警才从腰间掏出一串亮晶晶的小钥匙,嘁哩喀喳替他打开手铐:“安静!不许吵闹!等够一车人,就遣返你们回乡。”
逼仄的空间,多人拥挤的板床,缺油少盐的餐水,被关了两天,屋子里人越来越多。黄尘窝在墙角,昏昏沉沉。
又一黄昏,乌鸦在院外疯叫,它们好像在替黄尘鸣冤。屋内黑咕隆咚的,看不清碗里是什么饭食,黄尘一想到妻儿在家被催缴超生罚款,就更加坚定了不能被遣返回乡的信念,寻思着怎样逃跑。
“起来!起来!都起来!今晚就送你们回家!我喊到名字的,过来拿身份证!”看守他们的辅警一脚踹开门,大喊,房门发出破裂的咯吱声,哐当一声撞在墙上。
“我们要先上个厕所!”黄尘紧张地全身发抖,上牙哒哒地撞击着下牙喊一句,便在颤抖中紧闭嘴巴,用恐慌的眼神瞅着屋里其他人和辅警。
“对!对!回家要坐二三十个小时的车呢。我们要上个厕所!”
“懒驴上磨屎尿多。拿到身份证的,去!去!去!快去!解完手,直接上院子里的大客车!”
黄尘夹在拥挤的人群中,磨磨蹭蹭,趁着混乱躲到早就瞅好的,厕所旁边的角落,然后望着遣返他们回乡的汽车远去。
黄尘一口气抽了几支烟,缭绕的烟味,使空气浓稠得仿佛可以揉捏,就像那些挥散不去的往事,填满他的身体和灵魂。
03
午夜,无数的霓虹灯在远处闪烁,和隐约而至的乐声,令清冷的夜晚洋溢着盛世的信息。窝棚北端的一扇门“吱呀”一声被拉开,黄尘抬起头来,在黑暗中,望一眼工友出门撒尿的背影,他长叹一声。
晚饭后,黄尘早就想睡觉的,可他翻来覆去对自己说,不去学开采砂石的机动船,什么时候才能攒够两万元呢?为了儿子,必须干!一旦下定决心,那个淹死在钱塘江里农民工,浮肿扭曲的脸,又不断在脑海里浮现,令他不寒而栗。他再次捏了捏揣在贴身短裤小口袋里,薄薄的几百元,那个让他冒生命危险也要去开机动砂石船的声音,又强大起来。
黄尘在北京躲着没上遣返他们回乡的车,用藏在鞋底的钱,辗转至上海。在城里转悠了几天,也没找到工作。口袋里的盘缠越来越少,他不敢住宾馆,哪怕是最便宜小旅社的大通铺,他也舍不得钱。每晚睡在桥洞,用自己的血喂蚊子,好在是夏天,不冷。
出师不利,黄尘扛着行李,灰心丧气地徘徊在陌生的城市街头。有人凑近他,问他要不要找工作?包吃包住,如果好好干,月收入能上万。黄尘怀着兴奋又忐忑的心情,跟着他们走进一间封闭的房子。
那房子既不是工厂,也不是商店。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听课,跟着老师像打了鸡血似的喊口号,所有听课的人都被限制自由出入。
黄尘第一次听课,就觉得自己被骗进了传销窝点。看见想逃走的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怕了,努力装作很积极很听话的样子。十几天后,终于赢得他们初步信任,带他出去买东西。到了人多的地方,黄尘撒开脚丫子就跑,看守他的人边追,边大喊抓小偷。
酷暑骄阳在头顶燃烧,那一顿狂奔啊,如今每每想起,黄尘还心有余悸。他不敢回头,恨不能腋下生出双翼,飞过人群,飞回大山。“到杭州的,到杭州的,抓紧时间上车啦!”不知跑了多久,黄尘感觉自己都虚脱了,他毫不犹豫地跳上前面一辆招揽生意的客车。
身无分文,赤手空拳的黄尘,无暇欣赏落日余晖,面对钱塘江翻滚的波涛,使出喊山的嗓子,放声大叫。他那独特的乡音,引起同村的老乡的注意。从此,黄尘在武林广场的叶青斗码头落下脚。
一个多月来,他起早贪黑,汗流浃背,每天在码头卸沙。工作很简单,就是从砂石开采船上一锹一锹卸下沙子。劳动强大非常大,每人每天的卸载量都在一百吨以上。手上的老茧一次又一次被磨脱落,渗出血来。夜晚,坐着,站着,躺着都觉得浑身上下渗透着精疲力竭的累,那种苦非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和正确表达的。
黄尘在心底盘算,包吃包住,每天纯收入10元钱,如果是在老家天堂寨,那也是非常可观的收入啦!可是要攒够两万元罚款,怎么着也要三年五载,时间不等人呐!黄尘每次卸沙累得腰酸背痛,见开砂石船的农民工歇在岸上喝着茶,抽着烟,自在赌钱,就羡慕不已。
夜已深,江面上隐隐传来“沙沙”的响声,时断时续,又涨潮了。什么他妈的“钱塘郭里看潮人,直到白头看不足。”此刻,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黄尘,觉得一切诗情画意都是矫情,如果钱塘江没有闲人们喜爱欣赏的潮景,他也不必如此纠结。开机动船每天收入两三百元,一天收入抵现在一个月挣的,太诱人啦!时隐时现的潮声在加骤,少顷,潮水夹着轰响,在挤撞,在撕打,犹如黄尘内心两个敌对的声音不断猛烈撞击。
又快到月半了,未见潮影,先闻潮声。耳边传来轰轰隆隆的响声,江面仍旧是风平浪静,响声越来越大,远处,雾蒙蒙的江面出现一条白线逐渐移近,近,再近,白线变成了一堵水墙,随着一堵白墙的迅速向前推移,涌潮来到眼前。江水前来后涌,上下翻卷,潮头越来越高。每月的初一、十五都是钱塘江的潮汐,看这潮水的势头,黄尘在心底抱怨:今天只能开采早晨这一趟了,又少挣一百多。
经过几个月的磨砺,黄尘已逐渐适应了潮起潮落,不那么担心自己会葬身江底。他时常摸一摸渐渐鼓起的腰包,有种说不出满足和幸福,眼看就到春节了,他已攒了一万多元。他每月说到邮局寄钱回家,却从不真寄,一来为了省一笔手续费,二来他很享受这种腰包鼓鼓的感觉,虚晃一枪,只是怕别人惦记偷他的钱。
钱塘江的弯道较多,河床变化多端,砂石开采船所到之处,前一米江水可能还很浅,后一米就会很深,开采船很容易陷进漩涡,这是一重危险。另一重危险就是翻滚的江潮,好在现在已过了八月十五最迅猛的潮汐。
潮水前浪引后浪,后浪推前浪,潮头由远及近,遇到开采船这样的障碍,受阻被反射折回,会在江面形成一垛一米多高的潮峰,然后以泰山压顶之势翻卷回头,猛烈撞击开采船,形成回潮。顷刻间,潮峰喷珠溅玉,潮水灌进船内。
黄尘为了躲闪迎面而来的潮头,猛一加油门,调转方向,30多吨的开采船忽然猛地一倾斜,陷进沙坎,剧烈摇晃起来。黄尘冷不防被甩倒,船失去掌舵人,眼看就要被潮头吞没。
“我操!这点都稳不住!找死呀?”同船的老乡眼疾手快扔掉吸沙的棒子,一个健步冲到黄尘面前把住开采船的方向盘,怒火冲天,骂骂咧咧地大吼:“你他妈的不想回家过年,败(别)拉上我垫背!”
潮水铺天盖地的涨上来,声如狮吼,惊天动地,在开采船周围狂轰乱炸,淹没了老乡的怒骂。激流是无形的巨手,把开采船像乒乓球一样推来送去。船在沙坎中左摇右晃寸步难行,潮水仿佛要拼命地把船掀翻,推向死亡的深渊。嗖嗖的冷风,卷着潮水,形成一排水帘飞溅进舱,浸湿他们身上的棉衣,确有“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可摧”之势。黄尘吓得脸色煞白,两股颤颤,伙同老乡一起掌控方向盘,不敢掉以轻心。
早晨出船四个老乡还说说笑笑的,只一个潮汐,翻掉一只船,两个同乡说没就没了。深深的不置信感和无力感,令黄尘傻在那里。生命脆弱,命运无常,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天都黑了,尸首也没打捞上来。黄尘回想自己在船上遭遇的险境,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一个人若生了绝症,悲伤、焦虑、疼痛、恐慌,再历经各种治疗的折磨,最后绝望地哀嚎、离世,周遭的人和生病的人,也都能认命并接受。老乡却死得那么仓促和卑微,叠加的恐惧使黄尘头脑嗡嗡作响,心一下子崩溃了,只为每天挣两三百元啊,太不值啦!
喝!再喝!再喝!脱险上岸的黄尘和老乡喝得酩酊大醉,他需要用酒精来麻醉和平复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存的质疑。
宿醉醒来,黄尘毫不犹豫地扛上大包小包的行李,提前踏上春运的班车,车窗外一幕一幕安静地在眼前掠过,恍惚出门打工这大半年囫囵的日子。如果把全世界都放到眼前,他难以忘怀的还是天堂寨的山山水水,只有那里才有无数熟悉的面孔,而在无数熟悉的面孔中,总有笑盈盈的脸对着自己,向自己展露熟悉笑脸的,那就是家人。一路颠簸,多次转车换乘,终于又回到熟悉的村庄。
远远地,望见母亲拉着女儿小跑着过来迎接他。黄尘扑到母亲怀里,突然哇地一声,哭得山响,像牤牛似的,听的人瘆得慌。
那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在母亲面前流泪,而且毫无节制。眼泪是滞后的,悲伤是滞后的,那种劫后余生的悲怆,憋闷在胸,他需要发泄,需要大哭,需要痛诉,需要安抚。开砂石船原本有七个同乡,五人葬身江底。他逃逸似的从金钱驱动的城市回家,只有母亲和妻子的唠叨,以及孩子的哭闹声,才能缓解压在他心头颓败的凄惶和苍凉。
本刊编辑
赵克明戴晓东庄有禄王明军庆红
项宏苏恩李同好
值班编辑赵克明
美术编辑杨文民戴剑
江雨薇,本名江成进,女,七十年代生于安徽省六安市。安徽省作协会员,有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有中篇小说、散文和评论作品获不同奖项,并被收入一些选本。《分水岭》投稿须知
?可以是见诸报刊作品,但必须未在其它
转载请注明:http://www.yuncaibanjia.com/fjcf/110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