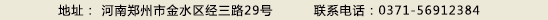许川夜读龚琳娜作品忐忑让我好忐忑
点击上方绿色图标,聆听本期《许川夜读》完整音频
看过网上流传一个笑话:高考语文填空,《神曲》作者是谁?有一个人填“龚琳娜”,另一个人说不对,应该是老锣。
被誉为“神曲”的《忐忑》,作者的确是老锣,创作时间是年。
那时它还远远不为大众所知,而且连名字都没有。我们准备做自己的一场音乐会,在中央民族乐团音乐厅,老锣专门按照室内乐的民乐风格写了一批作品,和它同期创作的,还有《静夜思》和《山中问答》,显然还是后两者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老锣把谱子交给我,告诉我这首歌是音乐会下半场的高潮,让我练习。我一看谱子,傻眼了——没有歌词,通篇都是拼音拼成的“咿咿呀呀哦哦”,而且不是随意写的,吐字发音和音韵节奏结合得很讲究。
“这是歌吗?”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和后来大多数人问的一模一样。不但歌词怪怪的,旋律还跳上跳下、绕去绕回,我一点儿也不喜欢。
老锣的态度不由分说:“我给你写的歌,你必须练好。练好之前什么也不要说。”作为工作搭档的老锣,很有点不怒自威的气势。
我们在多年合作中也建立起一种默契。我是演唱者,他是创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的老师。并非他的每一首作品刚开始我都喜欢,但我凭着信任和尊重去练,用我自己的办法,让作品得以更好的呈现。
关于这首歌的各种形容,比如“幽默”“夸张”“过瘾”,都是后来人们的评价。最初无论创作还是练习,我们都抱着做严肃音乐的态度。
我把它当成一首高难度的练声曲,硬着头皮去唱,把喜不喜欢的问题放到一边。越练越纠结,我的声带根本不适应这样的发声方式,唱着唱着就搅到了一起。
这种状态让我脑子里蹦出两个爆破音:忐忑。
掷地有声!
我问老锣:“这首歌叫《忐忑》怎么样?发音好听,意思对,字的模样也好看。”一颗心上上下下乱跑,跟我唱歌时的感觉差不多。
老锣说:“好。”
《忐忑》第一次在国内音乐圈引起比较大的反响,是我的老师邹文琴在保利剧院举办的“教学五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上。这场音乐会得到了邹老师很多学生的资助,我经济上不富裕,只有贡献自己的歌声,唱的就是《忐忑》。
唱完以后,圈子里炸了锅,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天哪,听你这首歌,我的血‘蹭’一下从脚底板窜到了头皮顶上!”
现场有中央电视台录像,但我的这首歌并没有播出,大概他们觉得太怪了。我也看了自己的演出回放,唯一的不满意就是眼睛太小了,像是没睁开。
从那以后,每天早上醒来和晚上临睡前,我都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滴溜溜地转眼睛。“在舞台上,眼神很重要。”我提醒自己。
练了半年,真的变化不小,眼睛变得更亮更灵活了,照镜子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更有神采。
年底,北京市政府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场新春音乐会。《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伦兵推荐了我和我的《忐忑》,于是音乐会总导演打电话到德国,邀请我回来参加演出。
我对晚会有抵触。因为过去假唱的经历。我想拒绝,但是老锣鼓励我要珍惜这次给中国观众唱歌的机会。于是,我心怀忐忑接受了邀请。
演出那天,我走上台,按照以往的习惯,先安静地闭眼片刻,感受现场氛围。天哪,场地那么大,人那么多!我想,我一定要把自己全部的能量都释放出来。
于是我在演唱中使尽了全身解数,包括一些从传统戏曲里学来的表现形式,花旦的身段,老生的唱腔,当然,还有苦苦练习了半年的转眼珠!不仅转,还要最大限度地转,不然怎么镇得住那么大的场地!我得让所有人都看见啊。好久没有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唱歌,唱得非常爽!
这场音乐会在电视里播出,是年2月,农历正月初五。
当我在屏幕中看到自己的脸部特写,都快晕过去了:两个眼珠子转得那么夸张,几乎对到了一起,用力过猛,不忍直视!
这下我是真的“忐忑”了,不知道观众看到了,会作何反应。好在当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但愿看见的人不多。
其后几天,并没有听到太多反馈,估计是那段时间各个台的晚会都很多,压根儿没人
转载请注明:http://www.yuncaibanjia.com/fjzl/10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