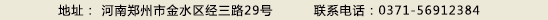张楚金鸡重金属
ZHANGCHU
作者简介
张楚,年生;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刊发表小说若干,出版有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在云落》《梵高的火柴》《风中事》《夏朗的望远镜》等,随笔集《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孙犁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
金鸡
文/张楚
秋天总是很短,仿佛黎明时墙壁上花卉的倒影。白昼也短,直至卯时杨树上的喜鹊才叫,而等我醒来,所有的鸟鸣声都消失了,只看到室友穿着肥大的睡衣趴在电脑屏幕前移动着鼠标。还不睡啊夜猫子?通常我礼节性地问候一句。修图,他略带羞赧地笑笑,轻声打个哈欠,头仰向布满细小蛛网的屋顶,点几滴眼药水。我挺佩服他。我一直不会自己点眼药水。这样会把身体熬坏的,没听老中医说吗?子时养肝,丑时养胃。没事啦大叔,习惯了,再说如果我偷懒,就真找不到工作了。
他搬进来也有段时间,跟上位室友相比,这孩子过于安静,睡觉不打呼噜,看《奇葩说》和《十三邀》时戴副AUDIOFLY牌白色耳机,即便外卖点的海鲜烩饭,碎龙虾壳吐得满桌都是,也像家猫般不出声响。他瘦,但不是枯瘦,眼大,但不瘆人。他还是个爱干净的孩子,临出门前总要洗澡,如果不洗澡的话就洗头。他用无硅油洗发水,他说自己是油质皮肤,而斯里兰卡的这款洗发水去油效果强悍,他尤其喜欢洗发后那种涩涩的犹如初恋的感觉。他还有三瓶不同水果味道的发胶和啫喱水,有一次我看到他在镜子面前小心翼翼地摆弄着发梢,半个时辰也有了。你要去拍戏吗?哦,大叔,他严肃地盯着我,你这话一点不幽默。发型对男人来讲太重要了!我忙活半天,还是没有办法将额头上的这一捋完全竖起来。他有些沮丧地掸了掸头发,一根根重新拽直。
跟他相比,我可真的老了。我从来没有买过除臭器,每晚将鞋子用油擦净后再郑重其事地悬挂在上面,我也没有像他那样,如果晚上不洗澡就用“小天使”牌柠檬味湿纸巾将腋窝擦拭两遍。他的袜子也比我多,有次我忍不住用眼光偷偷数了数,光夏天穿的短袜和船袜就有五十多双,更别提那些堆在床边的长腿棉袜和色泽鲜艳的足球袜了。
说实话,我甚至连瓶发胶都没有,当我为自己的邋遢寻找借口时,我才发觉我不是没有发胶,而是从小到大就根本没用过这种闻起来犹如空气清洁剂的奇怪液体。这就是代沟吧。代沟是什么?代沟就是我只有两双从超市买的廉价皮鞋,而他有三双手工复古尖头皮鞋、两双旅游鞋、四双板鞋和一双运动鞋。当他要走出那扇奶油色的房门时,他会根据自己穿的衣服选择其中的一双。
我们的作息也完全相反,当我睡觉的时候,他在设计平面图;当他睡觉的时候,我在图书馆看小说。只有中午,我们结伴去吃点东西。让我欣慰的是,他嘴不刁,这样,我们就能去离宿舍最近的那家小吃店。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店铺了,只有七八平方米,专卖成都小吃。据说他家的酸辣粉和红油抄手是学校里最地道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室友说的。你在北京根本吃不到这么正宗的酸辣粉,他吸溜吸溜地吞咽着银白粉条,艳红的辣椒油顺着唇角蜿蜒至下颌。老板,家是哪里的?老板正叼着香烟剥鸡蛋。他是个讲究人,手上戴着一次性塑料手套,只是我老担心烟灰要掉进盛满了猪小肚的铁锅里。
我是四川人。四川哪里的?成都。成都哪里的?蒲江。哦,我是青羊的。你娃儿是小老乡哦,加个蛋,加个蛋。我看到老板犹豫片刻后用勺子舀了个鹌鹑蛋大小的卤蛋,倒进室友碗中。
我才知道室友是成都人。他的普通话那么标准,丝毫没有川普那种软绵绵的桂花甜味。闭上眼,你会以为是电视里的播音员在一板一眼地念新闻稿件。
相对于室友的日常起居,我的生活规律得仿若机器人:晨七点起床,洗漱后去食堂吃早餐,通常是一碗豆腐脑两个煎牛肉包,要是煎牛肉包卖完了,我就吃两碗豆腐脑。上午骑着小黄车跑人文楼听专业课,我喜欢那个有点斜眼的老教授用西安话讲《中国文学通史》。中午小睡四十分钟,下午要么旁听历史学院的清史,要么躺在图书馆的沙发上读维特根斯坦。这套维特根斯坦全集共有十二册,我读了半年,连一本都没读完,读过的也半懂不懂。只记住一句话,“我只有放弃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施加任何影响,才能使自己独立于世界,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世界”。能记得这句话是因为我认为它从逻辑上讲是错误的……晚饭后我去体育馆跑步。我想学游泳,从十岁时就想学,想了三十年也没有学。当然,这次还是没去,主要担心被教练或年轻学员笑话,我自己都能想象到那种场景:一个松弛的中年男人挥动着黑毛手臂在水中胡乱扑腾,他以为自己是青蛙或蝴蝶,其实不过是头落水的猪。三个月后我彻底断了念想,每晚绕操场小跑十圈。初二时我曾在学校的春季运动会上拿过五千米长跑亚军,如今呢,跑起来倒像背上还驮着另外一个沉默寡言的灵魂。
我怏怏地想,这样已经很好了,这样能有什么不好?一切都将被细菌般的时光轻柔地吞噬、肢解、分离,变身泥土或尘埃……当然,吃饭是快乐的,只不过这快乐不关乎食物,也不关乎胃,它更像是厌食症患者的机械选择。
除了离图书馆最近的东区食堂,我最常去的就是那家成都小吃。店面委实小,又窝在阴面,白天也要开灯。老板跟他老婆在里面都要侧着转身。我时常听到他们用家乡话嘀嘀咕咕,虽绵软低沉,也能猜得出是在拌嘴。也难怪,夫妻店,连服务员都没有,他们又不是蜈蚣,他老婆还要时不时骑着电动车去宿舍楼送外卖。他们在台阶下面摆了四五张狭长洁净的小桌,顾客随便坐,有时我恍惚着老板真的变成了蜈蚣,瞬间长出了若干条手臂将一碗碗汤面甩到桌上。吃完后我通常吸支烟,吸完如果他们还忙得脚尖朝后,就帮他们端端饭菜,拾掇拾掇碗筷,反正闲人最不怕浪费的就是时间。
哎呀,你人太好了,老板大概想跟我握手致谢,刚探出却又缩回,胡乱在裤子上揩了揩。下次我要给你加个蛋!加个蛋!当然他说了也就忘记,翌日即便多加个卤蛋,也要收两元钱的。我倒没什么,很喜欢跟他聊一聊。通常是阴雨天,客少人稀,麻雀在草丛里觅食,他蹲在树下择葱洗菜,搓洗腐竹。他嘴上叼烟,时不时猛吸两口,烟灰落在洗净的蔬菜上。整支烟吸完,手连碰都不碰,当他“呸”的一口将烟蒂吐在地上,我才长长地呼口气。
你是哪里人,幺弟?我浙江的。你是学校的老师?不是。你是陪读的家长?不是。你是保安?不是。你是修锁修自行车的?不是。你是卖水果的?不是。你是宿管?不是。他这才乜斜我一眼,又叼上支娇子,你是扫厕所的?不是。他不问了,他不问了,我也就不说。我跟婆娘累得要吐血了,他抱怨道,腰杆都要裂咯。你们找个手脚勤快的老太太,花不了几个钱。他摇头,你晓得不,房租一年要八万呢,他伸出食指和拇指,狠狠地朝我比划。我感觉他把我当成房东了。下个月把我娃娃叫过来,反正毕业了,没个屌正事。闺女还是儿子?幺妹儿,长得嘿巴适。他得意地龇出口黄牙,唾沫星子差点喷溅到我脸上。
室友依旧过着黑白颠倒的日子。下午起床,起床了喝袋芬兰牛奶,然后穿着睡衣坐在硕大的电脑屏幕前。我老担心稍不留神,他的头部和躯干都会被电脑倒吸进去。他接了幼儿美术培训学校的活儿,说起来简单,给学校起个新名字。以前学校有两名股东,多年闺蜜不慎翻脸,一方另立门户,另一方要给新公司起个告别过去又展望未来的名字。我这才晓得这个长相颇似侦探柯南的室友有多神奇了:他把北京所有同类培训学校的资料搜集起来,按照所属区域、学校规模、学生年龄、学生性别、收费情况进行了索引。光这一项就花费了他七天时间。我忍不住问他,你是在做社会调查还是在起名字?
他说,大叔,这你就不懂了,要整合全部资源才能起个与众不同又醒目贴切的名字。这名字要高贵、要通俗,还要符合学校定位。瞧见没,就在国贸附近,国贸附近有几个高档小区?每个高档小区有多少户家庭?每户家庭是一孩还是多孩?户主是本地土著还是外来人口?这些都要综合考量……你收费很贵吧?他摇摇头,我刚出道,只收六百元。你别以为只是顿撸串的钱,如果跟客户建立了良好密切的关系,彼此信任,难道不是铺了条无形的路吗?你别小瞧这个培训学校的校长,好歹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她父亲是国务院参事,她哥是东城区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
后来他又接了个烧烤炉的平面广告图。他在烤炉上不停地更换着品种、色泽、厚薄度不同的牛肉、羊肉、猪排,将这些肉类的颜色变成浅红、绯红、深红、霞红、朱红、血红……你觉得哪种颜色看上去最有食欲?他忧心忡忡地盯着我。我只好说,你这是在卖肉,还是在卖烧烤炉?他说,大叔,你思维不能太僵化,看事物要看它的本质。我们去超市选择烤炉,首先留意到的难道不是炉上的食品吗?所有烤炉的功能大同小异,我们应该考虑如何让深思熟虑之后才去买烤炉的人如何在第一时间注意到烹饪后的奇妙效果,当他的味蕾在图片的催化下猛然苏醒并作出虚假判断时,他已经下意识地将烤炉抱在了怀里……
烤炉的平面图得到了老板的认可,但这个老板肯定不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烤炉都快上市了室友才拿到八百元设计费。他倒得意的很,大叔,我请你吃饭,去中关村的“河豚先生”,还是苏州桥的“第六季”?穷学生请什么客,省省吧。他笑嘻嘻地说,大叔啊,你不也是学生吗?别瞧不起我,我的生活费比你多。你以为我穷啊?偷偷告诉你,我家财万贯呢。我说,你讲话注意点,别闪了舌头,我以前可在税务局上班,要不,你请我吃红油抄手吧。他叹息一声,你们这些老人家,真是温良恭俭让,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还啥事都喜欢替别人操心,累不累啊?
那是深秋的午后。白杨树的叶子将黄未黄,天空是那种清冽的蓝,蔷薇还没开败,从破旧的栅栏里挣扎出来,我从花蕊里逮过几只灰翅蜂鸟送给玩滑板的孩子们。那天,还没到小吃店,远远就瞅到那棵粗大的白杨树脚下闪着团动来动去的黄金。走近了,竟然是一只公鸡。这是我见过的最雄伟漂亮的公鸡了,浑身一点杂毛没有,只有鸡冠是血红的,像涂抹在黄金上的血迹。
幺妹!一碗抄手,放香菜不加卤蛋!一碗酸辣粉,不放香菜加卤蛋!老板正在店门口抽烟,瞅到我们就梗着脖子朝店内喊。我问,哪里来的公鸡?老板说,幺妹来帮忙,把她的宠物也带来咯。果然,有个女孩匆忙走出来,慌里慌张地朝我们问,哪个加香菜哪个不加?再说一遍,我忘咯。她声音很小,像在跟人窃窃私语。室友瞄了眼说,随便,香菜我也吃的。女孩朝这边又瞥了瞥,没吱声。幺妹上的大专,在家里陪她奶奶,缺人手,才喊过来。老板嘿嘿地笑着,这个瓜娃子,傻得很。
我看到女孩走到白杨树下,从兜里抓出把玉米粒撒在草丛里。公鸡抖抖双翅,跳着脚过来,脖颈闪电般一探一缩、一缩一探,玉米粒顷刻就光了。我这才发现这只公鸡只有一条腿。我以为眼睛花了,不禁凑前瞅了瞅。没错,这只威武的公鸡只有一条腿。
小时被黄鼠狼咬掉了,女孩细声细气地说,别看一只脚,能飞到榆树顶顶高头。今年春天,还啄死过一条蛇。我们镇上的母鸡,都喜欢它呢。
再去看那只公鸡,又蹦跶着去草里觅食了。
把你的公鸡看好。室友用湿纸巾将每根手指刮得干干净净,盯着女孩说,把你的公鸡看好。
女孩呆呆地哦了声。
这里野猫特别多,比黄鼠狼还贼。前几天,我亲眼见到一只胖野猫叼着一只胖喜鹊蹿上树梢,啃得只飘下几根羽毛。
女孩瞪大眼睛瞅他,又快速瞅了下公鸡。
你用麻绳把它拴在树上,它就不会四处乱跑了。这学校,比你们蒲江还大呢。咦?你手上全是红油,还不快去擦擦。
女孩又哦了声,噘着嘴转身去收拾碗筷。
室友这段时间不再熬夜了,据他说导师要开个人画展,作为导师这届唯一的弟子,他要马首是瞻回报师恩,另外就是要写毕业论文了,必须白天到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这样我们的作息不免一致起来。不过白天他总是蔫头蔫脑,骑着小黄车跑完展厅跑图书馆。即便如此,他还抽空网购了熨衣板和熨斗。他将冬天的棉袜和长袜统统翻出,一只一只熨好,再挂在一个环形衣架上。他还帮我熨烫了我唯一的一件白色亚麻衬衣。你都这么大岁数了,难道只有一件衬衣?他张大嘴巴盯着我,你光膀子穿毛衣吗?我只好告诉他,像我这个年龄的,通常都会买若干件秋衣换着穿。他撇了撇嘴说,秋衣有纯棉的吗?你穿起来不剌肉吗?我只好再告诉他,秋衣里面还会套条跨栏背心。跨栏背心,他噗嗤一下笑了,跨栏背心难道不是打篮球才穿吗?我说我以前是单位的篮球队队员,13号球衣,人送绰号“罗德曼”,我打了三十多年篮球,跨栏背心也有四五十件了。他不可思议地凝望着我,半晌才嗫喏着说,天啦噜,你竟然还是篮球运动员……你有二百斤吗?我说我是虚胖,其实只有一百九十三斤。他也没接话,抓起桌上的香梨啃,啃着啃着扭头对我说,叔啊,你老了,但也要规划好自己的生活,不能将就,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呢。我使劲朝他点点头。
要是女儿还活着,应该比他小不了几岁。
深秋那段日子,我跟他频繁地去吃午饭。他们家又添了钟水饺、肠粉、凉皮和担担面。我们去了也不用说话,女孩就把面和粉端来,有时排队的人多,她就偷偷给我们加塞。我跟室友说,你发现没?我碗里的面还是那么多,但你碗里的粉的量明显大了。他就问,大叔,你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说很明显啊,这女孩可能喜欢你。他咧嘴笑了,说,难道你觉得我的情商是负数吗?我说你别太自负,仔细瞅瞅,女孩长得多好,大眼睛双眼皮……你对女人的审美还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打断我的话,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狐狸脸,这姑娘腮帮子上的肉也太沉了吧。我说,圆脸的姑娘有福气……他摆摆手说,我不敢谈恋爱了,怕了,多好的姑娘跟了我,她就不再是原来的她。为啥?都被我宠坏了呗。我还想问点什么,没问。他盯着杨树下的那只公鸡,心不在焉地说,真像是用黄金雕出来的。
女孩大概忙完了,去喂鸡,喂完了朝我们喊,你们忙不?不忙的话帮我录下“快手”。室友说,好啊,录什么?难道你也要生吞缅甸蟒蛇钢牙咬碎玻璃?女孩说,乱讲,“快手”不全是疯子,还有很多好玩的人呢,不要一棍子打死。室友懒洋洋地问,比如——。女孩说,有个小姐姐叫文静,住在内蒙古乌兰布统景区,养了一群狼,她每天跟狼嬉戏打闹,狼要是不听话了,她就把狼打一顿。室友说,哦。女孩说,还有个养牛人,是个牛经济,每天直播如何在牲口市场挑选好牛,又翻眼皮又摸牙齿又验牛粪的。室友歪头问,那你直播什么?女孩说,我呀,直播堂吉诃德跳舞,上树,爬寨子,捡项链。室友问,谁是堂吉诃德?女孩指着公鸡说,它呀,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配吗?室友干咳了声,问,你学中文的?女孩说,哪里,我学的织染专业。室友说,好吧,我们现在要录的是——?
女孩将脖子上的项链扔出去,然后吹了声口哨。我们看到堂吉诃德疯了般单腿猛蹿出去,直奔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饰品。说实话,我觉得堂吉诃德奔跑的样子很像饥饿的澳大利亚袋鼠。
天越来越冷,却没有下雪。来这里一年多了,只碰到一场雪。对我这样的南方人而言,不得不说是件遗憾的事。室友导师的画展结束了,结束当晚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晚宴,室友还把我邀请过去跟他导师同席,介绍说这是中国很有名的编剧。他的导师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热切地跟我握手、碰杯、加
转载请注明:http://www.yuncaibanjia.com/fjjw/10161.html